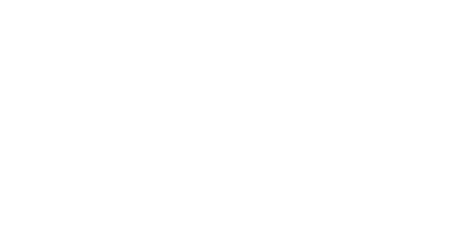文學創作
天同星,具有天真孩童的意象,也像修習瑜伽的過程。天同星讓我想起從前修煉瑜伽的日子——講究和諧、平衡與圓融,必須以柔克剛,動中返靜,最後回歸初心赤子,回到呼吸。
瑜伽動作多數取名都是向大自然致敬,種種招式的比擬,以動物為名,在瑜伽森林裡,鴿子、螳螂、獅與孔雀共存共榮;蜥蜴、海豚、駱駝及人面獅身眾聲喧嘩。一堂瑜伽課程大約會走完八到十個動作,像是演繹一座生態系。然而這些瑜伽動作的命名恐怕不只是描摹與虛擬而已,還有一種向萬生萬物學習的意味。
其中少有以人類為名者,但有一個稱為「快樂嬰兒」的招式:雙腳屈膝抬起,雙手握住腳底板,就像嬰兒在床上一樣,輕鬆而恣意。那是一種毫無包袱,輕鬆自然,由衷的快樂,彷彿能夠海涵所有的可能性;在嬰兒宇宙裡什麼都能發生,就像是天同星閃耀的道理:有量就有福。
「每個大人都曾經是個孩子,只是他們都忘記了。」小王子說。
復歸於嬰兒。大人們還得向嬰兒學習快樂,聖人無常師。
歷經社會化的大人,筋骨肌肉也隨著世故而僵硬,越是老練越是容易痠痛。修習瑜伽的過程,教練時常說:「我們還是嬰幼兒時,身體非常柔軟,任何瑜伽動作都相對簡單;長大了以後,伴隨年紀的,就是柔軟度與肌力的退化,所以要常常伸展。」
我想,天同的福氣正是來自於能屈能伸,上善若水,守柔不爭。
不知道老子的守柔不爭有沒有包含身體的柔軟?江湖在走,身段要有,謙卑與圓融已是通行世界的護照,人們懂得戒慎恐懼,卻沒有人真正在意肌肉的柔軟度,遑論靜下心來,叩問自身,返璞歸真。
天同星座落福德宮的我,尚不解晚年擁有未泯的童心是怎麼一回事;聽著老師講述特色為晚年有伴、福氣安泰、和樂融融,對照現今被職場和人際關係摧殘殆盡的自己,也只能苦笑接受一切都有最好的安排。也許生而為人,走過凡塵一遭,都還是難以了解生命的功課要引領人們去到哪裡;也如天同星的「天」字,每個人都帶著天命降生,只是際遇的差別。
「那都是過程。」老師總這麼說。
作為福德主的天同星,也許是要提醒我們:生命是一個循環,歷經生老病死,最終都會回到初始狀態,回首向來蕭瑟處時,心裡已無風無雨,都是過程。我想起了當年的瑜伽歲月,曾經學過一個艱難的招式,名為「胚胎烏鴉」。
那是一個看似簡易,卻必須極其信任自己的動作。讓身體蜷縮成尚在胚胎裡的烏鴉,少了翱翔的快活,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展翅前的黑,黎明之前最深邃的黑。僅是胚胎的烏鴉,也懂這世界的成住壞空,生老病死嗎?聆聽教練的說明,我也分神思考各種哲學問題。
教練仔細分解動作:先做一個「亞洲蹲式」,雙手合十貼於胸前,然後緩緩將手肘置地,再往前平放,直至小手臂完全貼合地面並且額頭點地,此時身形會像一個半圓的蛋殼。想回到原始的胚胎狀,還得經過瑜伽鍛鍊,哪怕自己不曾是隻烏鴉。
原本以為胚胎烏鴉很容易,實則不然。一開始的亞洲蹲式便已感覺身體的緊繃與不協調。對於瑜伽新手而言,嘗試那些悖離日常生活的動作最是困難,但悖離日常生活的動作,其實才是最「自然」的姿態。
這個蜷曲狀態讓我止不住顫抖,加上筋骨過硬,柔軟度欠佳,流了滿身汗才勉強支撐著。沒想到這還不是胚胎烏鴉的模樣,僅僅是預備動作。
待大家都能額頭點地,教練再次回到示範區。只見其將膝蓋抵住腋下,雙腳從原本的蹲地,到大小腿相併,小手臂仍貼於地面,用力一撐,騰空。教練的示範是如此輕而易舉,起初還以為真如其言:「這只是一個初階的瑜伽動作。」也是,畢竟比起那種更為嚇人的手不撐地倒立或大法師招式,胚胎烏鴉看起來還算溫和與友善。
一切就緒,確認好位置、姿勢、用力方式,我以為自己準備好復返為一個胚胎了,但一蹬再蹬,雙腳就是無法同時騰空。
是哪個環節出了差錯?讓這隻胚胎烏鴉連單腳離地都做不到?我反覆嘗試了好幾次,修正位置、姿勢、用力⋯⋯位置、姿勢、再用力⋯⋯仍舊失敗。平常有在重訓的我不可能沒有力氣,讓我鎩羽的,竟然是恐懼嗎?可是我連胚胎都還未及,何來羽毛可鎩?
我不想承認失敗,但離地的不安全感帶來一陣陣失衡,恐懼讓左右腳不聽使喚,只能一再奮力蹬起,又一再臣服於地心引力。終究只能在汗涔涔的反覆嘗試下,宣告失敗。
教練看著我的無奈,緩頰說著自己以前練習的經驗,練到都瘀青了還撐不起來。但瘀青不就是用力過度,反而失敗的認證?教練說:「那些過度用力,是恐懼與不信任。」無法撐起身體的瞬間,我在想著什麼呢?如果是恐懼,那我是害怕受傷,還是害怕丟臉呢?以及,如果我是不夠信任自己呢?
這個潛藏於心的問題,在幾年後的紫微課堂中,我有了暮鼓晨鐘的頓悟。
在瑜伽課領會的奧義,無論是用拜日式敬天,或是以輪式造橋,好像都很難真正成為英雄式中頂天立地的完人。光是一個胚胎烏鴉,都難以回到嬰兒般的初始狀態。天同星不只是一顆享福之星,更是告訴我們,真正的圓滿,是歷經過程後,無論悲喜,都能具有嬰兒宇宙般的海納百川。是福是禍,都有過程。
復歸於嬰兒,老子說。但除了不離常德,還要柔軟。我也想成為那個能夠直面恐懼的內在英雄。這次,我想為自己再嘗試一次胚胎烏鴉。